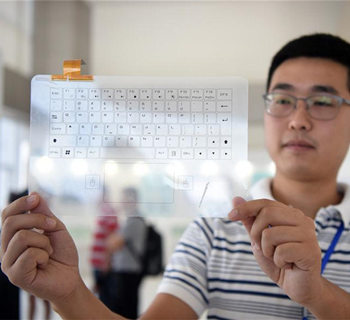-
在黑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透露了一个消息:他已经向上级建议,在适当的时候提出质询案,如果搞起来,将是人大监督的很大突破。
这是宪法第73条赋予的权力。不过,截至目前,质询案只散见于一些地方人大,全国人大层面至今还未举行过列入议程的质询。
宪法是这样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宪法强调,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
在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李元起的印象里,地方人大较有影响的质询案发生在16年前。2000年1月,在广东省人代会上,针对广东四会市对电镀城问题处理不当一事,25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质询,要求广东省环保局作答。
该局3轮答复均没获得通过,最终,局长被调离,一名副局长被撤换,质询案轰动全国。
然而,16年过去了,广东省人代会再无代表提出质询案。
李元起分析,质询案之所以少,原因一是先例少、经验不足,二是会期短而议题较多,三是质询是一种比较严厉的手段,人大代表直接询问其他机关领导人,领导人还要当面回答问题,影响比较大,启动比较慎重,有些地方还会考虑“给领导面子、给政府机关面子”,“大家都不好意思”。
作为宪法学者,他推测,人大如果要强化监督力量,可能会继续运用质询手段,“中国是绝对会用起来的”。既然人大代表想有所作为,“得把宪法实践下来,落实了”。
“质询有问责的性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韩晓武也提起了这个词。
在北京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他对人大的监督方式如数家珍,“按照法律规定,监督形式有7种”:比如,就某项专题工作听取“一府两院”专项报告;听取之前,人大会先做一些调研;当常委会委员提出建议和意见,“一府两院”的整改工作要在一定时间内予以反馈。
“如果这项工作改进不大,我们可以持续监督,比如下一次不听报告了,搞执法检查。”韩晓武说,如果整改起来困难,人大还可以在执法检查后再搞专题询问,如果专题询问以后还是改进不大,“那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我们还可以质询”。
自2015年以来,人大加强监督的步伐不断加快。
去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了《国务院关于2014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两个月后,中央要求,将审计查出的突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方式,由以往的书面印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改为由国务院委托审计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口头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史上的“第一次”诞生了。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了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张德江亲自出席联组会议。
到会回答询问的官员,有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副审计长袁野,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等7名“大员”。
“副总理带着相关部长回答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有关问题的询问。”吉炳轩回忆,专题询问现在是一年两三次,将来力度要加大,在监督的重点选题、方式方法和推动有关问题解决方面,“要下功夫,要有针对性”,“依法监督还要强化”。
吉炳轩还参加了执法检查。他发现,过去的执法检查,有些都是在法律实施了十几年后、二十多年后进行的,去年的执法检查,有的是立法10个月后就去检查,“对新的法律及时进行执法检查,跟踪贯彻落实情况,要比立法进行十几年后再进行检查效果好得多”。
人大监督又打了一次“组合拳”。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上,第一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担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并带队到地方实地检查;第一次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向常委会作执法检查报告,并主持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有媒体还发现,这是“第一次在全国人大层面,把执法检查同专题询问这两种监督方式结合起来”。
李元起告诉记者,这些是中国法治要求越来越高、法治建设强化的一个标志,以前有些监督进行得少与人大工作开展得不具体有关,“要把宪法好多措施制度激活了,不能规定了以后就在那儿放着”。
浙江省杭州市人大主任王金财说:“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他建议,法律实施满一年,必须报告书面实施情况,“我们立的法都要加强执法检查”。
今年,杭州市人大部署了查找杭州市地方性法规存在的问题,最终确立了7部法律需要提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另一个信号是,从2015年年初开始,多个省(区、市)发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大监督工作的意见》。在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上,也明确提出要加强县乡人大的建设。
人大监督如何增强刚性?在李元起看来,目前并不是没有法律手段,而是制度没有具体落实的措施。同时,在一些地区,人大代表的监督要排除各种阻力干扰,尤其是有些机关考虑到面子或其他问题不愿意让这种措施落实。
李元起说,代表大会都是会议期间发挥作用,但会后得有保障机制,得有一个落实的组织,“把这几个问题搞好,它的刚性就增强了”。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
【责任编辑:罗征】 -
相关文章
- [ 03-12 06 ]
- [ 03-12 01 ]
- [ 03-11 23 ]
- [ 03-11 23 ]
- [ 03-11 23 ]
- [ 03-11 23 ]
- [ 03-11 22 ]
- 热点新闻更多>>
-
- 微视频《答卷》
- 习近平: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
- 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建议
- 习近平通过视频欢迎全世界的朋友2022年相约北京
- 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亿万中国人民向世界发出邀请
- 习近平: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
- 人民领袖人民爱
-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三中全会将于2月26日至28日召开
-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 罗豪才遗体火化 习近平等前往送别
- 奋进新时代!习近平引领中国迎春再出发
- 2980名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确认全部有效
- 习近平告诉你《共产党宣言》的味道
- 中共中央印发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
- 十九届三中全会将于2月26日至28日召开
- 习近平: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
- 中国创新的时代答卷
- 中国为世界带来更多正能量
- 热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