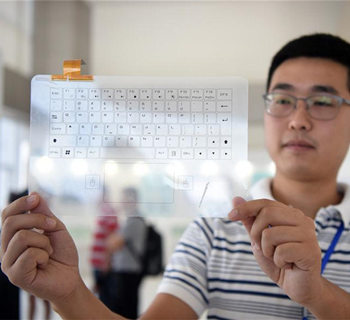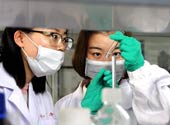-


没人能算出法国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下一步会站在什么位置。他曾经站在被称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茨奖领奖台上,也曾出现在纪录片导演的镜头前,照片还登上过时尚杂志。人们最近一次看到他,是在总统身边。新年伊始,法国总统马克龙首次访华,维拉尼是团队一员。
他跟总统的关系并非一向这么和气。维拉尼曾联合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给法国政府写公开信,公开抗议削减科研支出的决议,最终让总统妥协。近几年,他协助一些非洲国家成立研究中心,给当地儿童上启蒙算术课,还计划建造世界上第一个数学博物馆,使其成为“教育、科研和产业交汇的场所”。2009年担任法国数学研究机构庞加莱研究所所长后,他努力为同行争取研究经费,几年间为法国和国际数学联盟(IMU)募集到2400多万美元的捐款。
“人们常常误以为研究数学只是枯坐、冥想、奋笔疾书,其实这是一项极为社会化的活动。你可以在讨论、偶遇以及一系列机缘巧合中找到灵感。”维拉尼相信,数学家必须擅长与人沟通,需要“不断旅行,不断遇到不同的人,不断与他们打交道”。
十几年前,维拉尼就自学建立了个人网页,并在上面将玻尔兹曼、麦克斯韦、约翰·纳什和阿兰·图灵列为自己的“英雄”。这些数学家都以前所未有的创造性把数学的抽象应用到了经济学、物理学、计算机或工业界。
“在当代,数学家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通信理论、压缩传感、人工智能、图表分析、线性编程、流体模拟……数学在这些领域都有规模巨大的工业应用,并且拥有无限商机。”他希望通过应用,让数学能够真正融入人类社会。
跟大多数数学家一样,推动他前进的是数学的美。“法国人相信,任何一个问题都有普适的解决方式,信奉抽象和纯粹的美。”在他看来,数学是一门性感的学科,并且带来的愉悦会更加持久,“可以持续几小时,甚至几天”。曾经有人问他为何如此迷恋数学,他的回答是,“爱情无法解释”。
“美”是他生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他坐飞机一向只选择经济舱,因为“从统计学意义上来说,经济舱里的姑娘更可爱”。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做助理研究员期间,他每天都去电影院,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扑闪着大眼睛的奥黛丽·赫本。
站在菲尔茨奖的领奖台上时,他顶着一头齐肩褐发,定制的西装三件套上戴着袖扣和怀表,胸前巨大的胭脂红领结旁别着一只淡紫色的宝石蜘蛛。他有30多只装饰蜘蛛,其中不少是法国里昂蜘蛛工艺坊的师傅专门为他设计的。
他把玻尔兹曼方程看作“世界上最优美的方程”。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上学时,他一边在昏暗的走廊里散步,看着光线从一扇扇门下透出来,幻想着凡尔纳小说中“仿佛从潜艇的舷窗中透进来的一道道泛着冷光的波浪”,一边思考着如何把这个方程变得更美。“我们应当首先承认真实的存在,然后在真实的理论中欣赏美,而美反过来也会增加研究的动力。”
为了追求这种美,维拉尼长期忍受着混乱和沮丧的生活,2009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维拉尼几乎每天都躲在卧室,关上百叶窗,一圈圈地原地打转,脑子里全是朗道阻尼、正则化、牛顿迭代,跟别人说话最多敷衍几个字,甚至只是“哼”一下,在一旁忙着照顾孩子和准备晚饭的妻子都忍不住说他“太奇怪了”。
就连听报告时,他都会站在最后一排,只穿着袜子在地上来回踱步,“有利于寻找灵感”。中间休息时,他依旧只穿着袜子就匆匆赶回楼上的办公室,给合作研究者克莱蒙·穆奥打电话。他们之间7小时的时差为几乎不间断地工作提供了便利,维拉尼在普林斯顿工作到半夜,3小时后,身在法国的穆奥就能到达办公室,准备接手。相隔两地的两位研究者依靠电话和邮件彼此沟通,一个月的来往邮件可达两三百封。仅在离开普林斯顿那一天,维拉尼废弃的草稿纸就能装满4个纸篓。
一天清晨,在只睡了几个小时之后,他“清楚地听到脑袋里有个声音”“把第二项移到等式另一边,傅里叶展开然后在L2域反变换。”这是人类对等离子体的矛盾稳定特性完整数学证明的开始。他激动地骂了一句脏话。
几个月后,因为对非线性朗道阻尼的证明以及对玻尔兹曼方程收敛至平衡态的研究,维拉尼被通知获得了2010年的菲尔茨奖。领奖前,菲尔茨奖的评委会曾担心他会像格里戈里·佩雷尔曼一样拒绝领奖,他坦然地说自己“境界还差得很远,会痛痛快快地接受。”
他渴望各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由于菲尔茨奖只颁发给40岁以下的数学家,他在35岁的时候就仔细计算过,如果到2014年颁奖时,自己就超龄3个月了。“要想得奖,要么在2010年,要么将永远失去机会。”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
获得菲尔茨奖之后,维拉尼彻底成了一位“公众人物”。他开始频繁接受媒体采访,每年会接到成百上千个公开演讲的邀请。他还参与了法国申请2025年世博会的项目,与法国大厨、作家、宇航员、企业家和航海家一起成为了代表法国文化的6个人物之一。他也开始参与政治,在2017年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他当选为巴黎大区南部埃松选区议员,并且认为把数学与政治结合,是“必要且很酷的事情”。
在维拉尼看来,自己是在延续18世纪法国大革命留下的传统:知识分子要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也有责任发表观点。“毕竟,民主意味着参与。我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有责任为公共讨论作贡献。”
他希望用各种方式让大家明白,数学无处不在,它“改变了人们思考、解决问题和推理的方式,颠覆了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
“数学可能很抽象,但它并不无聊,它能够让我们测量地球的尺寸,观察看不见的原子,或是检测肉眼不可识别的微小形变。”他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如果你们只能从我这里了解到一样东西,那应该是:数学让我们超越人类的直觉,探索我们无法触及的领域。”
维拉尼把数学看作人类抵御机器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在的人工智能距离超越人脑还很遥远,它也许会下棋,但学会证明定理可并不简单。”他说,“也许需要人类担心的那一天终究会来,但在那之前,我们还有时间。”
【责任编辑:黄易清】 -
相关文章
- 热点新闻更多>>
-
- 习近平: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
- 中央深改小组第二次会议 习近平强调了三个“再”
- 习近平的“轻松时刻”
- 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
- 习近平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 习近平:坚守实体经济落实高质量发展
- 团干部的自我革命
- 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
- 习近平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 习近平致全国个体劳动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信
- 习近平信贺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开幕 贺信全文
- 习近平致信全国个体劳动者第五次代表大会
- 三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
- 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社会反响强烈
- 筑梦苍穹二十年——记“奋进新时代、筑梦写忠诚”的航天员群体
- 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 宪法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
- 高质量发展迈出一大步
-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 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宪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