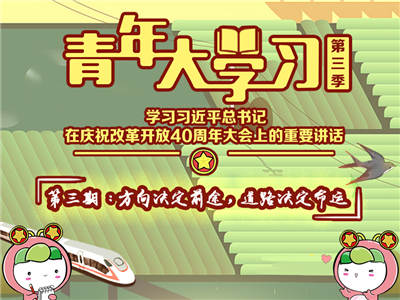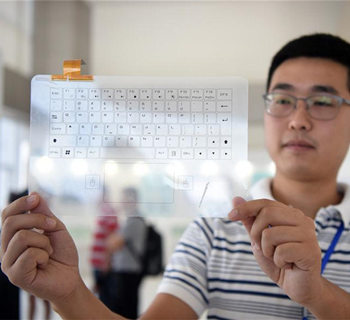-
美食无论何时依旧是串联起春节的密钥,由一碗腊八粥拉开了春节序幕,包着钱的饺子带来了春节的高潮。
-----------------------
当街上的小发廊、超市门口飘出“欢乐欢乐中国年,红红火火到永远”“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仿佛一个暗号,默契地声明春节就要来了。
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流动,在拥挤的地铁上放空,有时候格外怀念家乡过年的热闹。沿着回忆的滤镜溯源而上,曾经的年总是别有一番风情。
快过年时,小孩子们总是反复唱到一首民谣 “新年到,好热闹。贴春联,放鞭炮。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嬷嬷买个木疙瘩,老头买顶新毡帽。”一颗心雀跃着,怂恿家长给买鞭炮,买零食。
但往往以小孩子的心性,难以将好吃的留到过年那天,总会忍不住先买些解解馋。盘算着今年自己能收到多少压岁钱,想想那个数字还挺美滋滋的。于是舍得大出血一次,拿出自己攒了一整年的10元私房钱,悄悄地在村头的小卖铺里买包跳跳糖,买几根辣条,再揣上几包“唐僧肉”,然后和小伙伴们一起跑到秘密基地,瓜分零食。心满意足地吃完,还要紧张地抹抹嘴,互相问一句“我脸上还有东西吗”,然后一阵风似地野着回家。
回家后,看到大人正忙东忙西准备年货,炸好的黄澄澄的丸子、酥脆的带鱼,香甜的果子棒……一只小手蠢蠢欲动想偷偷摸一个,正在和面的妈妈总会及时拍下,先呈出一份祭奠神灵,然后才允许我去“污染”剩下的。
炸丸子的过程中,是绝对不允许小孩子捣乱的,小孩子多嘴几句“为啥炸了这么多丸子”,都会让旁边的大人不悦,像驱赶麻雀一样把一群小孩子撵走,下一年甭管有多好奇,也不会自讨没趣,乐得做一个贾宝玉式的“富贵闲人”,只是可惜,这个“富贵闲人”也就当了那无忧无虑的几年。
从镇上的小学、县里的初中到市里的高中再到省里的大学,那个曾经炊烟袅袅、邻里亲密的村庄与我渐行渐远,村里的小洋楼也一栋栋拔地而起,麦田一点点减少,家乡的人懒得再自己炸丸子、炒年货,直接买超市里做好的多省事……一切都朝着快速便利看齐,但总觉得少了那么一点味道。
大学时候回家,去集市采购年货的路上,常见到路过在冬日墙根下穿着新衣、戴着新毡帽的老头儿老嬷嬷,时光仿佛很悠长,他们把手揣在袖子里,懒洋洋地晒着太阳,见到来人,总会眯着眼,然后口齿不清地缓缓念叨到“哎,这是谁家的姑娘,都长这么大了”,听到声音,我总会放慢脚步,暂时停住,笑一笑打声招呼:“嗯,王奶奶,新年好,我才回来没多久。”
后来每年回去,墙角石凳上坐着的老太太老头儿就会少几个,从奶奶口中,我听说哪位老人年前去世了,谁又被闺女接去照顾了,看着你长大的人在慢慢离你远去,从此,那条回家的路上少了些乡里乡亲的关切,而我行走的脚步也越发匆忙。
如果说年味的消散是商业化潮流下的必然趋势,那么在乡土文化走向没落中,童年也在逐步消逝。过年时,家里的弟弟妹妹、侄子侄女每人手拿着一个手机或者Pad,还是盯着屏幕不放松,再也不会像我们从前那样在麦田里肆意撒欢,在泥土路上追逐嬉闹。他们的春节,已不再土味十足。
但美食无论何时依旧是串联起春节的密钥,由一碗腊八粥拉开了春节的序幕,包着钱的饺子带来了春节的高潮,那吃几个便会腻口的元宵与老鼠偷喝油的面灯标志着春节的落幕。虽然比起奶奶口中的“当年过节”已少了很多年味。无比庆幸,那缕“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温暖依旧。
除夕晚上,一家人围绕着八仙桌,桌上必须摆上成双的菜品,成双的碗筷,每人捧着一碗饺子,暗暗比拼谁能吃到包了钱的那个,讨个吉祥如意的好兆头。吃完饭后全家搬着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嗑瓜子,聊聊天,熬着岁等到凌晨1点放鞭炮,这些约定成俗的习惯如同渗入血液一般,默默恪守一年又一年。
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无忧的岁月,已经远离,从前慢的故事再难讲到下回分解,而有些人也注定只能封存于过去的回忆里。迁徙、流散、失落、痛楚,混杂着快乐、单纯、奋斗与美好,在乡土文化的衰落与童年的消逝中,春节变成了一个符号化的存在。它是一个仪式,更是团圆的信仰。
只是年纪越大越对过年少却了期盼,多了焦虑。因为蓦然回首,发现自己也到了被催婚的年纪。从问成绩排名到问对象收入,毕业后的春节过得步步惊心。在七大姑、八大姨的围攻之下,唯有淡然哀叹一句,“婚否,婚否,我还是单身狗”。而明年的春节,在不变的新年氛围之下,不知道这个答案会否有所转变。
【编辑:黄易清】 -
相关文章
- 热点新闻更多>>
-
-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卡塔尔国埃米尔访华并同其举行会谈
- 习近平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
-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 暖心微视频丨在一起的味道
- 习近平的幸福年心里话
- 总书记的牵挂·一枝一叶总关情
-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感召两岸同胞同心圆梦
- 习近平来到我家“拉家常”:生态好了,日子红火了
- 习近平为什么强调“底线思维”
- 习近平给领导干部上的“公开课”
- 习近平就菲律宾发生爆炸袭击事件向菲律宾总统致慰问电
- 连续7年共迎新春,习近平与党外人士的心里话
- 两部门部署开展2019年传统节日文化活动
- 这项“紧迫课题”,习近平因势而谋
- 以稳求进 以进固稳
-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 习近平为何一直重视“创新思维”
- 习近平与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互致新年贺信
- 习近平来到我家“拉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