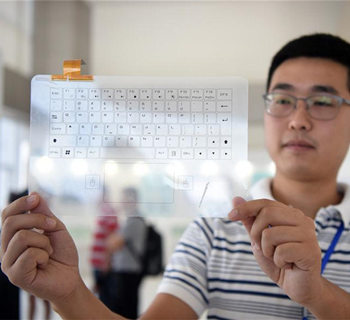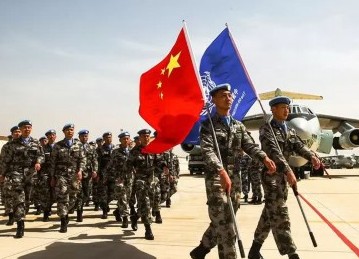-
条条大路通戛纳。这是一场殿堂级的电影盛会,但在记住参赛电影之前,人们倒是先被几个作妖的中国网红“吸睛”。
瞧瞧这条60米的红毯展示的生物多样性,有“乡镇桃花大仙”“金甲哨牙战士”“雪纺纱裙扮回春大妈”……让我想起小品里牦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赴京表演的全部阵容,造型一个比一个雷人,表情一个赛一个劲爆。据说往年有个网红姐在红毯上一摔成名,回国都有人接机了。
拼,应该是这些网红的必备素养。“流浪大师”一露面,众多小网红收拾行李买张机票即刻前往,把沈巍围在一个角落,以明媚的45度角举着美颜手机,近得能看见网红们的线雕鼻头。
光拍照那本事不算大,有举牌子要嫁给沈巍的,有自封“师娘”的,还有叫他“爸爸”的。因为不堪其扰,沈巍闭门谢客,一众流量主则在门前唱歌的唱歌、劈叉的劈叉,群魔乱舞,如杂耍场。
千万不要小瞧他们,能在网红经济的红海里扒拉着人头爬上岸,这都是成了精的。现在随便走在街上,都能看见如出一辙的整容脸,娇滴滴地举着自拍杆走过,他们大概率飞不上金字塔的顶端,没人记住他们,也没人在意他们,空留玻尿酸,一把辛酸泪。
人们厌恶网红,但也眼巴巴地羡慕网红:他们直播一小时礼物抵得上一部电影片酬,试色口红带货高过机场街拍明星,一个个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怎么就轻松拥有了豪车名表,与偶像谈笑风生,为什么我就不能赚点快钱?
头部网红需要具备很多资质,要拼搏,要能吃苦,甚至可能要有点人格障碍。
德国人博尔温·班德洛写过一本叫《隐疾》的书,副标题是《名人与人格障碍》,讲名人有自恋型人格障碍,“一个自恋者靠别人的赞赏而活着,他全部的追求就是别人的敬仰,崇拜或欢呼,他幻想伟大的成就,无限的崇拜,爱情,做爱,美丽,魅力和权力,借以激励振作自己。”而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精神科医生。
你看,那些直播网红不管背景如何,关键是得放得开,感觉自己是圣女化身,万众敬仰,仿佛晃着胯骨轴子走在巴黎时装博览会的天桥。无论路人怎么躲,也要毫无惧色地堵上去,回头就说遇见粉丝了。
网红的自恋还体现在“蹭”的艺术上。看见带点名气的都要蹭一下,并且蹭得理直气壮,丝毫不怯场。
路遇明星能跟踪,脚踩粉黛乱子草,一起学猫叫狗叫“奥买噶”。
脸长得不好看也要自信,还能走吃播派,镜头对准大嘴,炸鸡、披萨、辣条一一排开,大口咀嚼吧唧嘴,人们也能迅速爱上你。
对于这类“患者”,理想的职业是演戏。只要有观众就不可遏制地要演起来。精神科医生说,他们多多少少有些幻觉慌语征候,不可遏制地想成为中心人物,故事几乎张口就来,真真假假,但都意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个人形象,因此很多这类病患有孜孜不倦的写作热情,甚至是狂热,因为故事的主角就是他们自己,顺便还做了自媒体。
如果不是强大的内心自恋,你很难解释为什么工作人员都劝说了,戛纳红毯上的网红还能气定神闲赖着不走。你也同样搞不明白对一个陌生流浪人员喊爸爸,并搔首弄姿是出于何种心理。
像我们这样的社交恐惧症患者怕是难以获得出名的要义,博尔温·班德洛把名人比作玻璃缸里的金鱼,随时都要接受所有人兴致盎然停下来驻足观看。如果别人不看,那就得拼命吐泡泡、摇尾巴、甚至跳出鱼缸以自杀式式行为引来注意。
自恋型人格障碍与生俱来,如果戴安娜不是王妃,她也许会是个抑郁、暴饮暴食、自我残害的购物狂;如果梦露没成为明星,她没准儿只是个流落在好莱坞街头的兼职妓女。他们不是被名望所累。不同类型的人格障碍,决定了他们的一生。
还记得初代网红芙蓉姐姐、罗玉凤吗?她们打开了自恋的阀门,敢拍敢说,老娘就是智慧就是美。那时人们未见风物,颇嗤之以鼻。现如今网红的舞台刀枪剑戟,分外精彩,中国人民确实见过世面了。
把那些精神上有过人之处的人,放进流量的浪潮里冲刷,后果可想而知。他们在摄像头前充分展示表演欲,不放过任何一个赢得关注的机会,要么红,要么疯。
厚一次脸皮就能涨几万粉,卖几十万张面膜,叫一次爸爸就能上热搜,就有金主求合作。即使不是天生戏精,也要不断给自己加戏,以求活在粉丝们的首页。毕竟这年头,丢脸挨骂都不可怕,怕的是没人知道、没人议论。
网红食人气、饮流量,有了关注加持便更添“丑”的自信,流量是他们的内增高,流量是刷在脸上的散粉,有了它们你就敢出门,敢自恋,敢作妖,敢以天地为舞台,吸五常之人气。
【编辑:贾志强】 -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