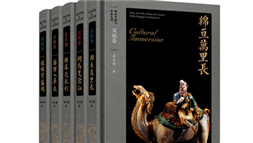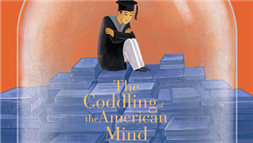离开江西湖口的前一天,我在舜德县青竹村又一次坐上救援船。
那几日,因为鄱阳湖迅速“长胖”,185座单退圩堤进洪,很多村庄一夜变成了一座座“孤岛”。救援船成为他们的交通工具之一。
湖面辽阔,白鹭扑腾着翅膀消隐在林间,不知名的灰色水鸟在水面点了几下,掠过长空。如果不是半截屋顶、垂至水面的电线在身边掠过,会错以为这里几个世纪都是这副模样。
水底下,静静地躺着稻谷、豆角、棉花、玉米,鱼儿在饱餐。大水冲走了养殖户的鱼,也招来了大批钓鱼的人,有人欢喜有人忧。
来江西湖口前,7月7日,我和视频组同事前往安徽歙县,报道高考因洪水被推迟的消息。
在安徽黄山,人们回忆起的是1996年的一场洪水,老人们能清晰地说出洪水淹没到楼房墙壁上的某个位置。一位老人,向我们回忆起1954年的洪水,洪水吞没了她家乡安徽无为县的土地,一家人流离失所,父兄皆在途中去世。即使垂垂老矣,她讲述此事时依然痛哭流涕。
歙县洪水退去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快。没想到,一些应届生对高考延期一天感到新奇、兴奋,不是见证历史,而是一不小心成了“历史”。
7月9日中午,一位送考生的家长在考点外告诉我,自己是孩子的大姨。洪水冲进了他们的店。孩子这几日住校,本来以为可以瞒住他,但接考车正好路过他家门口,孩子还是看见了一切。晚上,孩子连打了4个电话,询问家里的情况。
她说,平时遇到高考这么大的事肯定是举家送考,而如今她只能作为“家长代表”来看一眼,让孩子安心,他的父母还在清点损失,收拾残局。
无意中刷到的一条短视频揪住我的心。一座484岁的老桥被洪水冲击,短短几秒内轰然崩塌,视频里,连呼的几声“天啊,天啊”,突然击中了我。我们决定,寻找这座老桥。
老桥在屯溪,桥边拉起了警戒线。一位五六十岁的女人,撑着一把伞,在石板凳上踮脚张望。那时,还没有见到桥的真貌,但是通过她,我们“看见”了桥。
她告诉我们,自己特意过来看倒塌的老桥,是因为“就像自己家里一个亲人去了一样”。10岁时她住在江北,上学在江南,天天从老桥上走过。如今60岁的她住在江南,父母的家在江北,每次去看父母时,也会特意绕道从桥上走过。
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十几岁时走老桥去买煤饼的经历。老桥斜坡陡峭,她拖着笨重的大板车,在很远的地方就开始跑步助力。
说着说着,她的泪水就盈满眼眶,她说:“老桥不像博物馆的文物束之高阁,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在那短短的一个小时内,我们先后遇到了一对年轻的父子、一位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小学老师、一对此前住在这里的夫妻等人。他们听闻老桥倒塌,前来凭吊。警戒线内站着的执勤人员,虽然不动声色,但默默允许我们去拍摄几张老桥照片。
老桥形体已逝,我惊讶于这座小城里的人们对老大桥的感情。在我眼前,这群屯溪人个个化身为诗人,嘴里蹦出充满灵感的语句,有人记得在古桥石头缝里肆意生长的野草,有人想起桥头出现过的古董铺、卖时令瓜果的小摊、还有近几年出现的弹吉他的年轻人。头发花白的老人,则会背诵起一首郁达夫途经屯溪所作的《屯溪夜泊》,“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
三位老人和孙辈来到与老桥隔空相望的新桥上,随身带着厚厚一摞照片。每逢春节、中秋时,这个四代的大家庭团聚,都会以老大桥为背景拍一张全家福。这个家族越来越大,子孙繁茂,有人去了北京定居。
三位老人不约而同地跟我讲述了同一个故事:老大桥曾见证过他们的父亲第一次骑自行车的样子,那时还是“大少爷”的父亲,和别人打赌,跨上当时最时髦的自行车在老桥上骑了一个来回,最终在接近终点处摔断了手。
在这座与老桥平行的新桥上,三五个陌生人遇见都能侃上两句关于老桥的大山。
在一篇论文里看到,“集体记忆是族群认同的基本依据……集体记忆的消失则注定造成共同体的孱弱、分裂和覆灭”。我们在屯溪待了整整5天,围观了一场大型集体回忆,直到老桥的倒塌又成为人们新的集体回忆。
老桥的回忆还盘桓在屯溪人的头脑中,7月13日我们匆匆转场,溯流而上,来到九江湖口。在前一天7月12日10时,长江湖口站水位达到22.49米,超出警戒水位2.99米,距离1998年最高历史水位只差10厘米。
那时,我对“单退圩堤”这四个字感到陌生。站在一处已被鄱阳湖水漫过去的堤坝上,看到鱼儿在内湖努力向鄱阳湖扑腾,只觉得又涨了知识。
相比于鄱阳湖周边的鄱阳县、江洲镇,湖口县显得太过平静,连在社交网络上也找不多太多受灾信息,只有一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马影镇淹得很厉害,但是目前过不去了”。我尚未看到一个具体的受灾的人,当时差点想写一篇“湖口没有新闻”,又安慰自己,湖口没有新闻是件好事,但又质问自己,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在湖口的第三天清晨,我赶去湖口县南部的流芳乡和一位跟随救援队而来的同事会合,前往一个村子的“渡口”。渡口其实是在一片已被淹没的农田边缘,我们穿上救生衣,跟随救援队员去给被困村民送米送油。
第一次坐上橡皮艇,我才知道这种不自然形成的“湖泊”,对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也是一种挑战。橡皮艇的螺旋桨很容易被水下看不清的渔网、豆藤缠住,失去动力,稍有不慎可能翻船。有点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即使公路被淹了,橡皮艇遵循公路的轨迹走起来才是最顺的。
我们最先到达一个村子,台阶上站着的几乎全是老人,但实际上那是二楼的平台,一楼已经躺在水底下了。我有点懵了,问:“可是我在网上没看到你们这边被水淹啊。”一位老人苦笑着说:“水一下子就涨上来了,都忙着搬东西到二楼,谁还有时间拍视频咯。”
那时候我才知道,洪水两次淹没他们的村庄,当时已断水断电了好几天。第一次大雨造成的内涝一下涨了3-4米,但退水快;第二次是单退圩堤进洪,为减轻鄱阳湖及长江的防洪压力,他们和他们的生活成为“牺牲品”,而这场水,可能要历经数月才能退去。
一位老人说她的手机没电了,也没地方充电,安置点也不想去,“因为没有做饭的地儿,只能吃泡面”。老人们半夜睡不着,就在一盏靠太阳能发电的路灯下聊天,因为那是晚上唯一还亮着的东西。
村子和外界联络的方法就是靠两位还算“年轻”的中年人划船出去采购物资。而那所谓的“船”其实就是将两个轮胎绑在木板下制成的“轮胎船”,划动的桨只是两块不到半米的小木片,这是他们1998年也曾用过的老办法。
看我目瞪口呆的样子,一个60多岁的大叔专门下水坐上去演示划动技巧,我和其他老人站在岸上看着,都笑得很快活。但是过几天,我听说附近一个被淹的镇上,一个坐着自制橡皮艇的农民,不慎淹死在水中,我笑不出来了。
当我回到乡里时,乡干部带我们去了一个设置在幼儿园的安置点。三间大教室每间住着10余人,正值午后,大多数老人在睡午觉,孩子们拿着水枪相互打闹。
后几日,我们又去了另一处也因单退圩堤进洪大面积被淹没的舜德乡青竹村,那里的村民生活还算不错——因为村庄自1998年后搬迁至高地,这次没有断水断电,且先后有救援队和消防队专门负责接送村民。
一位一直守在渡口的小哥告诉我们,他此前在外面跑外卖,这两年回来做扶贫产业,种植豆角和养鸡,但如今豆角全都淹在水下了。他家的两头牛也淹死在洪水中。
他的大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具戏剧性的“救牛”故事。大水涨上来那天,牛倔强地站在田埂上不肯走,他的父亲下水救牛,水一直漫到脖子。牛救回来了,他的大伯赶过去,没见到弟弟的人影,以为已经遇难,望着水大哭,直到弟弟出现在身后,他才反应过来。
人没事,是这场洪灾带给村民最大的安慰。在新闻里,这些单退圩堤的贡献是“降低鄱阳湖水位20至25厘米”的数据。但是数据背后,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有的人倾家荡产,有的人没了一季的收成,他们或多或少地承受着洪水带来的损失。
当我们到达青竹村时,洪水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因为无事可做,村里跳广场舞的时间提前了几个小时,中年妇女在“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的歌声里苦练舞技;屋后麻将声也与蝉鸣声此起彼伏,年轻人和老年人凑在一处发呆聊天。
我们跟着救援船,遇到跨越洪水去养猪场实习的大学生,也迎接回带着一堆游戏安心地去过“孤岛生活”的中考生,还有“乘风破浪”去被洪水围困的寺庙里做法事的老人。那位年轻的扶贫小伙从外面买了一大包咪咪虾条——这是他的儿子点名要的。生活还在继续。
他们见过不少洪水,但从未预料过今年会有这么大的洪水。他们担忧下半年的晚稻能不能种成。以后怎么办?只能等水退下去再看。
我再次去到一处村子旁最近的单退圩堤上,在我眼中鄱阳湖和内湖水位依然相差无几,但是带我前去的村干部兴奋地说,“内湖水好像退了10厘米”。在他们的村子里,养殖珍珠蚌的人每天都在试图抢救自己的珍珠和池鱼,水涨1厘米,他就把养珍珠的网拉高1厘米,水退是漫长的但也是可期待的。
7月22日,我从南昌乘坐飞机返北京,天气晴朗,从万米高空可以清晰地俯瞰鄱阳湖,湖中有几段长长的堤坝,其中有一截也许因洪水没过而消失不见,也有一些地方水退留下一片土黄色的“冲积平原”…… 我想起一位水利工作者的话,人类和洪水本就是一个共存的状态,你不可能把它堵死,也不可能造起100米高的堤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