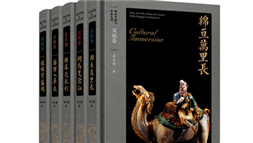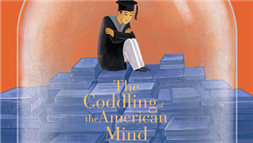野狼搜救队正在山间寻人。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供图

野狼搜救队在打捞溺水者。

搜救告一段落,队员十分疲惫。

队员王荣平和家人。

搜救队夜间出动。

野狼搜救队的装备。

野狼搜救队部分成员。

电焊工高友顺。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摄
他们被称作“民间110”,他们不属于任何一支正规队伍。
他们的新“办公室”是公墓山前建起的两间房屋。杭州富阳野狼公益搜救队的“狼头”陈青伟做墓碑买卖,家里门面是搜救队的早期据点,一边摆着救援用的绳索,一边是样品骨灰盒。
队员几乎全来自农村。瓦匠、电焊工、猎人、酿酒的、养鸡的、卖二手车的、安装空调的、开小超市的、开烧烤店的、派出所协警、村卫生院医生,七七八八的人把自己装进统一的墨绿色队服,自掏腰包寻找失踪于山水间的人。
野狼搜救队的教练之一是孙海良,他是一支大型民间救援队公羊队的正式成员,去过地震的尼泊尔、台风后的莫桑比克。公羊队全球有千名队员,救援设备包括声呐、潜水装备和一架直升机。
野狼队则几乎没有走出过富阳,救援集中在山地连绵的新登镇,装备包括一艘补丁缠身不得不“退役”的救生艇;自制的水下捞人铁钩;以及禁猎后,从猎狗项圈上取下的定位装置。最具科技感的是一架无人机,在一次夜晚搜救23名驴友的行动中丢失,葬身绿色丘陵地带。
“跟他耗,耗到天亮,人也许就活了”
新登多山,富春江支流绕过,在晨间形成谜一样的雾气。山上有竹子、野杨梅和野猕猴桃,每到清明和秋季,失踪率上升。
“我们像打猎的,只是不知道猎物是什么。”野狼搜救队多半搜救对象是老人,也有迷路的驴友和离家出走的孩子。有时找到失踪者,对方摇着头,满脑子是“我要死了”。搜救队员的第一句话是告诉对方“你还活着”。
去年刚过完年,一位65岁的老人跟家里怄气,带着饼干和一包烟,消失在山里。傍晚接到消息,队员们放下碗筷,从各自的村子赶到老人最后现身的地点,有人开面包车,有人开轿车,有人骑摩托,全在显眼的位置贴上了野狼搜救队的标志。
教练孙海良分析,老人跟家人吵架,很可能去寻死。“寻死会去自家山头,不会给别人找晦气,而且会死在山的南面。”
队员们需要在相似到乏味的山间寻找不一样的痕迹,最明显的是烟蒂和饼干袋,还有他采过野果的痕迹、脚印的痕迹。登山客背着重包,脚印的后跟陷下去深;山民走路用前掌,不会用脚后跟。驴友背着包,走过折断的树枝在腰间,山民折断处要高一点。
若是寻找失踪了几天的人,脚印上是否有树叶,树叶上是否有灰尘,都是判断时间的线索。虽然黄金救援时间是72小时,但如果第二天中午还没找到人,教练孙海良认为有一半概率已经发生意外,“如果有一群鸟飞上去,我们怀疑下面是不是有吃的(尸体),还有一群老鼠突然逃窜。”
有时,家属会祭山神,坚持往算卦指出的方向寻找。搜救队员有自己的逻辑,“我们会跟家属、邻居、村里爱说八卦的人和村干部分别了解情况,判断对方是什么样的人。”“狼头”陈青伟说。内向的人走路会犹豫,狂妄的人走得快,体力不好的人会横着走,不会直直往山上冲。
晚上8点,12名队员开始上山寻找,相隔5米横式排查,搜索过的地方用绳子标记。在去往老人自家山头的路上,发现两颗白菜被踩过的痕迹。
教练孙海良通过对讲机告诉所有人不要发出声音,他站在山上开始呼喊老人。这是寻找失踪几小时内的人最简单的方法,对方一有回应,队员们就可以听音辨向。
山坳吞没了回响,没有人作答。夜晚的山静悄悄,动物经过的声音让人提心吊胆,“这山上有野猪和毒蛇。”有时月光从林木稀疏的地方洒下,被困山上的人兴奋地奔着亮光而去,脚下可能就是悬崖。
许多年前,孙海良在山上寻找一个采茶女无果。后来人们推测,采茶女摔下悬崖,落在石缝里,被树叶盖住,当天一场雨又冲掉了痕迹。孙海良曾在事发地100多米的地方搜索过,闻到尸体的气味“像一种农药”,他放了烟寻找风源,但山坳里的风自顾自打转,线索断了。3年后,采茶女的头盖骨被雨水冲到路边,人们循迹找到遗骨,只剩一双雨鞋没烂。
搜索持续到夜里11点,队员们被撤下,亲属们换上继续找,范围已经缩小,“肯定就在周边”。
过了半夜,家属也无进展,冬天太冷,一行人决定第二天早上继续寻找。次日,野狼搜救队刚要出发,接到电话,说老人躺在竹林的一块石板上,喝农药死了。
“发现尸体的地方距离我们寻找的地方不会超过300米。”“狼头”陈青伟说,“如果我们当时再找找,他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教练孙海良判断,老人前一天故意躲起来,所以他才换上亲友去找,“想感动老人”。“那天晚上不应该休息,跟他耗,耗到天亮,人也许就活了。”
在野狼搜救队38次救援中,没有找到的情况是少数,成立3年里,60人被找到,3具溺水的尸体被打捞上来。
今年5月,“狼头”陈青伟生日那天,一位电缆工人在水库溺水了,有人扔了竹竿给他,但没有挑到,溺水者挣扎了几下,水面恢复平静。
队员在等红灯时换上队服,快速到达现场。6名队员抬着80公斤的冲锋艇下水了,用自制的铁钩网格状寻找。先勾上来一只袜子,后来找到了人。
“狼头”看到,溺水者全身像瓷器一样白,双手紧握在胸前,“最后的希望,没有抓住。”尸体被抬上来的一刻,“嘴里、胃里的东西瞬时性吐出来了。”陈青伟没多想,回家后妻子李晓芬埋怨道:“你生日好弄这个事情的哦。”
“虽然人也不在了,早一分钟找到,少那个一下。”陈青伟33岁,个子不算高,头脑灵活。他十几岁时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与一位好友一同去考军校,对方考上了,他没考上。两人约定,将来当兵的要混个“一毛二”(指中尉),留下的要当个小老板。两个人都实现了梦想。
陈青伟拍照时总是站得笔直,喜欢迷彩,管村民叫“群众”。他带着上小学的儿子在烈日下站军姿,“想培养他上军校。”每次搜救队出任务,时间允许都要列队报数。“所有人的肩章都是一样的,不分级别。”
他曾经向往体制内的工作,在民政局工作过几天,“开灵车”,后来继承了家里的墓碑生意,在凌晨4点半起床到附近送货。“可能是生活过得太平静的缘故”,前些年,他爱上户外运动,参加冬泳协会,2017年,他建起了这支搜救队。
“我做过最叛逆的事情是把送货的车改成救援车。”他在那辆金杯的车顶装上探照灯,车里装着急救箱和救援锁具,后半截车厢用一块铁板隔开,可以放进救生艇,“有时沾上死的鱼虾,臭死了。”
跟天斗,跟地斗,最好还是退三步
教练孙海良1999年开始做驴友,给自己起网名“雕”,最酷的一张照片是在雪山之巅光着膀子做飞雕动作,“显示我能与天斗”。
2008年元旦,一行7人准备穿越四姑娘山,那里属于青藏高原邛崃山脉,山势陡峭,主峰海拔6250米。按年龄,孙海良排老大。他们登到三峰的最后一个营地,准备次日登顶。夜里两点,突然下起漫天大雪。
山峰呈60度,白雪皑皑。凌晨4时,7个人准备动身。从营地到山峰需要6个小时,必须在中午12点前抵达,不然风很大,“容易下不来”。
一路上,雪不停,人爬出去3米又被风吹回。在距离山顶500米的垭口,7个人决定“算了”,“在顶上绝对站不牢”“危险系数太高”。大家本为登顶而来,7个人都很遗憾,指着山峰顶说,“来年再登”。
第二年,体重190斤的老四执意要去。半个月后,孙海良得到消息,“老四进四姑娘山,没出来。”
他遇到了雪崩,登山杖扎在对面的山上,留有他的血型和电话。“我们当老四活着,他的QQ,我们6人一直维护。”他们打开亮着的头像,总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老四非如此不可。“你与自然抗衡,抗不过,你只能献出生命。”
教练孙海良不是爱冒险的人,只要有两成危险,他就不去挑战。每次穿上救援服,识别危险的雷达立马开启,“得先有危机感再去救人。”
他给“野狼”上的第一课,就是如何保护自己。“千万不要跟自然抗争,跟天斗,跟地斗,最好还是退三步。”他的三个朋友是游泳高手,一次看到金沙江虎跳峡水流平稳就跳了下去,“差点没上来”,一个人眼看就要被水吞没,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抱住了一块石头,从此听到“金沙江”三个字便会不自觉发抖。
“驴友的失踪也是因为盲目,对自己的体能没有真正去考量,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是对生命的挑战。”孙海良年轻的时候想当个小老板,在国企里做领导。他现在每天坚持打太极,懂中医,拥有一家药店,每个周末都外出散心。
2008年,孙海良开始接触公益救援,3年前成为“野狼”的教练。他教队员们看等高线,不用专业术语,“纹路密集的地方就是悬崖,像树上的疤。”他还教他们如何急救、怎样用绳子岩降,但最重要的一课留给安全。他要求大家救落水者一定不能毫无准备单独下水,对方会把你当做最后一根稻草死命往下拽。“大家来做这个事情也不是赚钱来的,要是伤残了,家人会不会伤心?”
攀登用的主锁100多元,一旦掉在地上听到响声就不能再用。绳索被脚踩过也报废了,它由一股股细绳组成,脚下的沙子进去了,承重时,会像一把刀一样割断绳子。
孙海良每一次随公羊队出征,都要签生死状,一切后果自己负责,跟国家和队伍无关。他参与了几次国际救援,常遇到别国的“熟面孔”,他们对危险保持警惕。“德国人很严谨,工具的大小和箱子都是严丝合缝的。”有一次五国救援队员联合演习,孙海良习惯性把仪器靠墙,日本人提出,在真实的野外,仪器要向外,方便随时拖走。
云南鲁甸地震时,孙海良在田野的帐篷里给灾民量血压,余震来了,灾民背了血压计就逃。人们睡在地上,对不定时的危险保持警惕。灾区生活苦中作乐,灾民拖着救援人员去家里吃饭,在塌了一半的房间里喝一杯茶,主人就很高兴。
救援结束时,当地的傣族人背着花生、糯米把救援车前前后后塞满。汽车发动,老人、小孩在路边跳起傣族舞,车子开了很远,他们还在跳。去西藏救灾时,孙海良的脖子上堆满了哈达;在尼泊尔临行前,人们朝他们摇头,大家开始时不解,后来才知道在当地,摇头表示尊敬。
孙海良今年54岁,膝盖因登山而凸起。前不久,他才参加完鄱阳湖水灾的救援,感慨体力不可避免地下降,“我最怕有一天,我报名参加救援,结果第一梯队没有我,第二梯队没有我,第三梯队还没有我。”
他始终记得自己第一次参与救援,失踪者是27岁的小伙子,妈妈独自把他带大。救援队员去山里搜寻,那位妈妈拿着快餐面等在一旁,见有人回来,总是先问“儿子找到了吗”,大家摇头。她把快餐面端到大伙面前,说“你们辛苦了”。
从第一天到第十一天,那位妈妈一直没哭,接过快餐面,孙海良哭了,“她来的时候满头黑发,刚才一低头,头顶已经有碗大的一圈白发。”
救援出的是体力,即便最累的时候,人没找到,“你也不敢看家属的眼神。”
“是我人生最积极的时候”
孙海良所在的公羊队去年一整年没出去过,“最好没任务,我一穿上这衣服,就面临大难。”野狼搜救队不一样,他们解决当地人出现的意外情况,“实际是老百姓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
新登镇派出所副所长裘科慧说,当地一个月平均有一起老人走失,全所只有30名警力,分散在不同条线。“野狼”有40名队员,能上山下水,“没有他们,我们动不动就要全所加班。”
解救老百姓的同样是老百姓,在人群里毫不起眼。队员高友顺穿着电焊工服赶到桥头,有人要自杀,好在及时化解了。更多时候,他要脱下工装,赤身在水里寻人,不管冬夏。
电焊工高友顺54岁,离异,独居,脸上总是红红的,可能跟长期做电焊有关,家里的桌子上摆着他为队里做的捞人铁钩。他小时候也有个当兵梦,听说侄子当了兵,“我买了好多烟花,沿路从家里放到镇上。”
“高友顺在路上看到堵车了,他会把车停一边下去指挥交通。”队友说。他不富裕,别人请客他不去,宁可在家吃泡饭。网上跟人聊天,他用摄像头拍拍四面墙,“谁还愿意跟我交朋友?”他因为投资失败欠下20多万元,但为了救援方便,凑钱买了辆车。
一次紧急打捞落水者,高友顺正在厂里上班,请了假去救援,他把衣服一脱赤身跳入水中,回来被厂里主管责备“脑子进水了”。他说话嗓门大,眼里容不下沙子,索性辞了工作。
早几年,高友顺跟随另一家救援队去过山体滑坡的四川茂县,“整个村没了,100多人埋在下面。”他看着水上漂浮的残肢,哭了一场,找来香烛,在大石头上拜了拜。
他有一个女儿,不常见面。高友顺决定死后捐赠遗体,女儿不肯签同意书,他说,“人死了被喂狗也不知道,不如捐了还能做个教材。”遗体拿回后,他要女儿一把火烧了,撒在富春江里。
虽然离婚十几年了,他跟前岳父岳母常来往,“我反正自己父母也没了,我叫了这么多年爸爸妈妈也叫惯了。”
他爸爸患有阿兹海默症,一个大雨天,老人沿着河沟走,被风吹到河里淹死了。
他父亲生前也走丢过,像他搜救的很多老人一样。有一次一个老人走失,队伍找到晚上12点。第二天下起大雨,搜救队刚上山,老人自己走下山了。看着老人泥水交加的脸、破损的衣衫,高友顺想起自己的父亲,父亲走的那天也是一样的风和雨,不一样的是,老人还活着,正拿着棍子打树上的雨水。
和电焊工高友顺一样,队员李桥生家里也不富裕,前妻带着孩子跑了,但他们保护尊严的方式不同。
李桥生的家在山脚,几根竹竿歪歪扭扭支在门前,架起几件衫,他最爱穿的就是搜救队的短袖衣服,无论是做泥工、木工,还是油漆工、水电工,印有“野狼”字样的衣服像长在他身上,脱不下来。
一进他家门,最显眼的货架上摆着各式各样的酒。空调上落了一层灰,电线被老鼠咬断很久了。家里的8条狗和4只猫进进出出,比人热闹,“没人要,我就养在那里。”
他总是坐得直直的,引以为傲的是救人的本领。他从小水性好,23岁时姐姐盖房子找他借点钱,他在送钱时路过一座桥,听到有人喊救命,衣服没脱,穿着皮鞋跳下去把人救了上来,“后来我把一沓50块给我姐,叫她自己晒一下。”
周围人觉得他好面子,爱夸大事实,日子过一天算一天,但遇到救援,他的心是热的。
有个年轻人借了网贷,家人帮着还了一笔,他又去借。后来写了封遗书,人就不见了。李桥生和队员追了一天一夜,鸡圈、猪圈都找了,水塘也找了,“有时候我们把跟他有矛盾的人家里冰柜都翻了”,正要放弃的时候,发现人躲在一个老房子里,身上盖着农具。
很多队员把野狼搜救队的紧急任务群置顶,里面不允许闲聊,任务一来,紧跟着一排“收到”。队员陈小波可能是最积极的一个。
陈小波40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他喜欢戴鸭舌帽,下巴上长期挂着一撮胡子,手臂上有辟邪文身。朋友叫他“野人”,他在队里的名号是“孤狼”,骑着摩托车独来独往。他差不多是爬山最快的一个。“我不开心就去爬山。”
“孤狼”陈小波17岁离家出走到北京游荡,没少犯错。
以前为了赚钱,他带着6个上海大学生在云南的原始森林里户外探险,结果迷失,28天没有出来。“没有待过的人不知道山上的夜晚有多恐怖。不说别的,鸟叫一声,周围黑黑的,心里就有压力。”
他们喝竹筒里的水,把水藤上下砍断,拎起来接水喝。食物是打猎到的野兔、溪水里的小螃蟹,烤烤吃了,还有树上的虫子。胡子长了,陈小波就用刀割掉。10多天时,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绷不住了,骂起来,“你给我们带死了”。陈小波扇了他两巴掌,“你扰乱这支队伍,给我清醒一点。”他心想,这是一座山,不可能出不去。
“孤狼”陈小波给大学生们分配任务,有人去找笋,有人去找干柴,“一开始笨手笨脚,后来不用我说什么,没吃的了,他们主动会去找。”突然一次,一个女孩被蛇咬了,毒牙还挂在鞋上。“最简单的处理方式是用刀割开,清洗坏血,再用蛇草敷上。有毒蛇的地方,不出20步就能找到草药。”好在咬的是鞋跟,人受伤不重。陈小波一脚踩住蛇,把它吃了。
第二十八天,有人听到猎人的枪声,陈小波心里清楚,他们得救了。几个人马上叫起来,对面山头有了回应,当地的少数民族最终带他们走出了大山。
“出来的第一件事是找吃的。”把手机充上电,有的家长已经在云南寻找他们了,几近崩溃。陈小波对一位父亲的话印象深刻,“你们这帮孩子,经历了这个,以后怎样做人应该懂了。”
他现在开了家烧烤店,起名“野狼烧烤”,店里挂着李小龙的画和他救援得过的奖章。“是我人生最积极的时候”。
“我一开始是进队里玩玩的,有点约束不自在。”多救几个人,他的感觉不一样了,“这像份职业,现在不是玩,是时间和生命。”他看到老人摔在山上,全身泥巴,身上沾着尿,“你觉得又可怜又心酸。”
一次晚上有救援任务,烧烤店里正忙,女友不想他走,“她不知道轻重,只知道赚钱。”以前两个人一起开店,第二天女友不来了,二人分手。
有人失去工作,有人失去爱情,但大家都不想离开这支队伍,“除非有一天残了,帮不上忙了。”“孤狼”陈小波轻盈地跳上一座山,摘下野果。
民间救援“大比武”
每次救援结束,“狼头”陈青伟就把参与行动的队员名字发在朋友圈。年底,他自己做了“公益爱心之家”的牌子挂在队员门前,“毕竟没有工资”。他指着15面锦旗,“我们也就这么一点点荣誉”。
副队长史荣平擅长分析信息,杭州女子失踪案时,他曾去现场排查监控死角。副队长朱关金开了家饭店,是队员集会的场所,老婆常见他半夜回来,脚在鞋里泡得很白。王仙勇和王荣平是两兄弟,房子盖在一起,母亲只有这两个儿子,他们结伴去救援。陈杭出生于1997年,是队里最小的,也兼职做森林消防的工作。后勤部部长袁君其外号“员外”,胖胖的,出钱多过出力。钟新儿是队里少有的女将,大伙叫她大姐,负责财务。
田间地头出了什么麻烦事,“野狼”一抵达,“狼头”陈青伟听到围观群众嘴里说着“野狼来了”,眼睛放光,好像事情即将得到解决。那种时刻,他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价值感。
教练孙海良看到这群游勇“以前可能是捣蛋鬼,现在终于挺起胸”“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更不会跌下去”。他有时在队伍里点个名,夸赞谁进步了,被表扬的人头总是抬得很高。
“狼头”陈青伟跟妻子开玩笑,等到自己80岁时,可以自豪地跟孙子谈起,“爷爷那时候是个勇敢善良的人,救助了很多人。”
今年年会,队员们把家属请来,自己端菜收拾,开了12桌宴席,主题是感谢家属。“没有家属的支持,大家不能随时出发。”“狼头”陈青伟说。
尼泊尔8.1级地震的前一天,教练孙海良的妻子刚因乳腺癌开完刀。那是公羊队第一次国外救援,孙海良在病床前犹豫,电话一个一个打进来。妻子看了看他,“你不要想了,你去吧。”
知道孙海良要去救援,医院几乎整栋楼的护士都对他说“放心去,我来管”。在震区的第五天,妻子发来信息:检查结果,阴性。“我坐在那里,攥紧拳头浑身收缩,我在灾区不能笑。”他颤抖了几下,血液在体内快速循环。他只把好消息告诉了队长,二人撞了3下拳头,“善有善报”。
一天下午,“狼头”陈青伟忽然对妻子说:“李晓芬,我们要到安徽去了。”前段时间安徽有洪水,队员们热情高涨想去救援,电焊工高友顺第一个举手,说自己随时能走。
李晓芬照顾着店里的生意,也照顾家庭孩子,她看看丈夫,只问了一句,“你考虑队员家属的意愿没有?万一出点意外,你担得起责任吗?”
副队长史荣平说,最怕有谁脚扭一下,出任何意外,“一旦涉及经济纠纷,队伍就散了。”“野狼”队员虽然买了意外险,但没有任何官方的保障。
教练孙海良遇到过许多民间救援队,能力参差不齐,一些队伍“抢尸体,抢功劳”,在重灾现场,不够专业的队伍会造成二次伤害。他说,官方正在举办民间救援队的“大比武”,考察实力,便于管理。
未去安徽救援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设备跟不上,“我们的冲锋艇适合在平静的水域,而且我们也没有专业的救生衣,那个要1000多元一套。”上一个冲锋艇报废后,“狼头”陈青伟“要饭一样”拉来一些赞助,最多一笔4000元,买了一艘1.2万元的冲锋艇,不得不在艇周围贴上不同的广告,“要是去安徽破损了,我要被队员说死了。”
当初买队服时,队里就出现分歧,有人不愿意花几百元买一套救援服,平时也穿不了几次。几经协商,大家最后选择了迷彩队服,队名用魔术贴贴在背后,平时干农活的时候一撕,也能穿。
队标是“狼头”半夜起床在纸上设计出来的,“我很喜欢狼,有灵性,又有团队精神。”他在搜索引擎上找狼头,抠下来,又加上了登山杖和闪电,代表民间户外和快速出击。
有一次山上寻人,向导走太快,“狼头”陈青伟跟丢了,手机没有信号,GPS也失联。小竹子密密麻麻,望不到天。陈青伟找路时,忽然发现头上有两条竹叶青,“啪”一下飞过来。
“我拿个小木棍推到一边,”他开始着急,对讲机里没有队友的声音,“队员遇到蛇怎么办。”天已经暗下来,他忽然觉得害怕,他怕兄弟们无法走出大山,那种恐惧甚于毒蛇和夜晚。
当对讲机终于传来熟悉的声音时,陈青伟默默哭了,信号一个连一个,将这群人串在一起。下山后,他没对任何人提起自己的崩溃。
救援最幸福的时刻是把人找到。队员们一边往下撤,一边说笑,“那种笑容,平时不太容易看到。”他们有时在救援现场对着江水吃泡面,有时在饭店包间庆祝胜利。窗外,富春江水平静流过,青山依旧。人们举着酒杯,面色通红,每个人都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