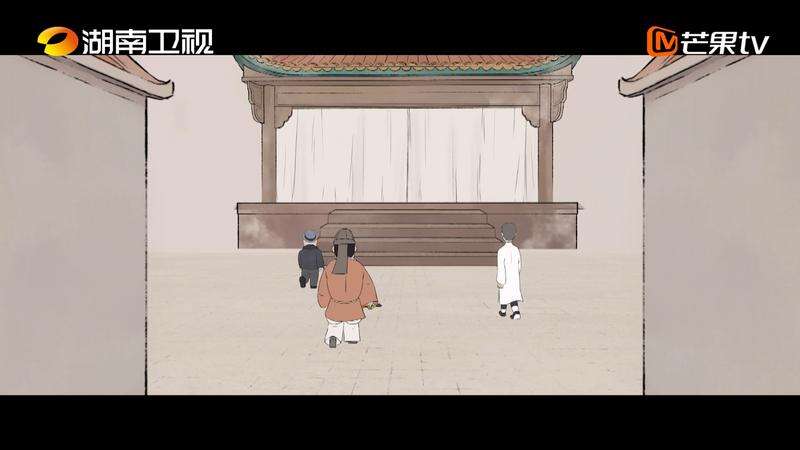飞旋的温烙歌
酱油是乡愁的解法

早在成为网络流行语之前,“打酱油”对一个85后小孩来说,就是人生的重要一课。攥着妈妈给的钱,提着厨房调料区“C位”的酱油瓶,到离家一两百米的小卖部,打一瓶散装的酱油,是我最早的“社会实践”之一。不是油,不是盐,偏偏是酱油,不知道为什么。
20多年后,从江南北上工作的我,在一个老乡的出租屋里,看着他打扫厨房,从橱柜深处搜罗出高高低低五六个酱油瓶,排成一溜。并不热衷也不擅长厨艺的他,酱油拌饭却是饭桌常客。由于经常找不到“上一瓶”,于是就有了“这一排”,口味相当稳定。
最近有部纪录片《酱油是什么》,简单直白的片名和关键词,一开始真不知道怎么还能拍8集。但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东西,往往像一座冰山,浮出海平面的是不经意的琐碎日常,而海水之下是深不见底的文化历史。酱油是一种调味品,但对中国人来说,又不止于此。
历史、科学、工艺、食用,纪录片主要讲了酱油这4个方面,展现了一颗黄豆变成酱油的全过程。
酱油,要从“酱”说起。
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朝,中国人就吃一种叫“醓醢”(tǎn hǎi)的调味品,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酱”,不过那时候都是肉酱。醓醢怎么吃,周朝人很严肃。在礼仪场合,不同食物要搭配相应的酱。孔子说: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没有适配的酱,后果很严重。
鲜,作为中国人对美食的终极评价和追求,正是制酱的重要目的。现代人知道,蛋白质发酵可以获得鲜味。所以,酱的发明也许并非偶然,那是古人为了追求鲜味而摸索出来的发酵魔法。
从肉酱到豆酱,是中国人饮食史上的一大步,具体这一步迈出于什么时候,没有明确记载,但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不少豆豉和豆酱。这一转变的意义,还远大于饮食本身。以至于日本的文化人类学者石毛直道在定义“东亚文化圈”时,用了这样一个词——“豆酱文化圈”。
说了这么多,都是为酱油的出场作铺垫。终于,在距今1400多年前的北魏时期,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的制酱工艺,其中提到“澄取的酱清”,就是今天所说的酱油。但别急,“酱油”这个词,还得再等600多年。
南宋时期,有个叫林洪的读书人,中过进士,擅长诗文书画,但青史留名是因为他是个“吃货”,著有菜谱大全《山家清供》流传至今。这部书中记载了4道小菜——柳叶韭、山海羹、山家三脆、忘忧虀。别看小菜平平无奇,其做法中提到“酱油”,是目前我们已知的“酱油”这两个字最早的出处。
同样成书于南宋的《梦粱录》中写道:“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有人认为,这里的“酱”指的是酱油。酱油从制酱时的副产品,历经唐宋300多年的变革,终于独立“出道”。
到了明朝,医者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提到了酱油的制作工艺。
《酱油是什么》赴哈尔滨、北京、上海、长沙、佛山等8座城市,细细品味不同地区对于酱油的使用差异。碰巧,这些城市我都去过,印象最深的一是上海,一是佛山。
形容上海菜有一个词——浓油赤酱,这个酱,就是酱油。上海用酱油,肆无忌惮。上海红烧肉,酱油要用到有点发黑才算好。
相比之下,佛山用酱油,精打细算。据说一个合格的粤菜厨师,至少要掌握四五种不同酱油的调配方法。有的粤菜厨师岁数大了,干不动了,但凭着自己的一道酱油秘方,就能够维系生活。和味蕾相比,语言在体验酱油时显得十分匮乏。
寻常人家做饭没有酒楼厨师那么多讲究,但在我妈的厨房中,也从来必备生抽、老抽、蒸鱼豉油3种酱油。我家的餐桌上,白斩鸡、清蒸鱼、白灼虾,都得单配一小碟酱油,那是点睛的灵魂所在;至于油焖笋、卤鸭、梅干菜蒸肉之类的菜,酱油的用法用量,更是一个家族的秘密。如今,这个秘密已经传到我的手里。
大学时去国外交换,做红烧鸡翅时,我口中念念有词,“生抽提味,老抽上色”,这是我妈谆谆教诲的口诀,说大了,大概也算文化传承。这一道红烧鸡翅,在当时的公共厨房中,奠定了我在各国留学生中的地位。
酱油是最具中国特点的调味品之一,培养了我们的味觉记忆。也许,酱油就是中国人的乡愁,或者是,乡愁的解法。
蒋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