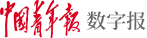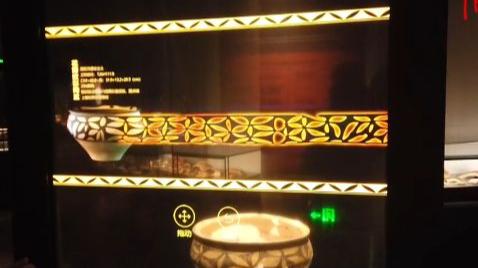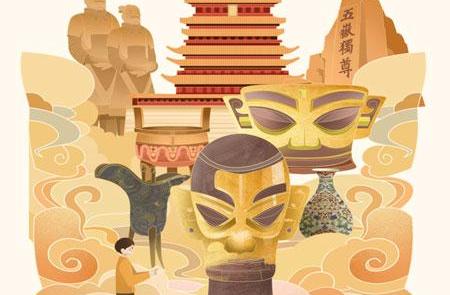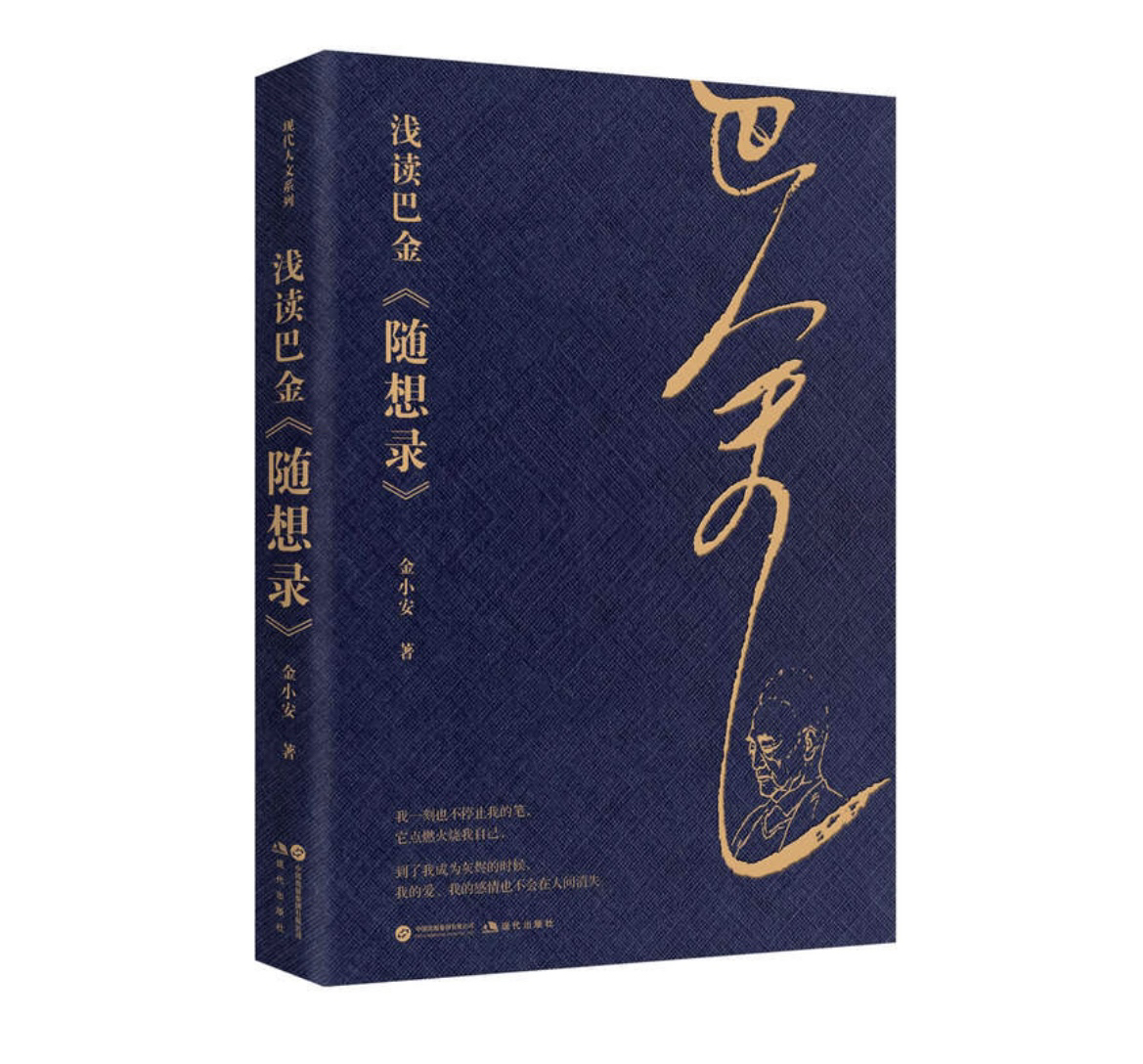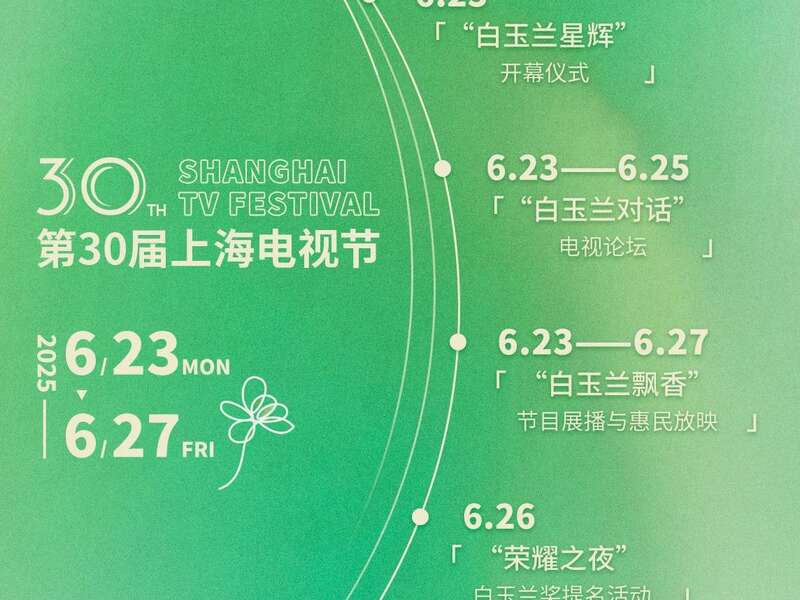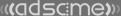跨越“死亡谷” 科技成果“转”机在哪
“考虑在天津落地吗?我是天津发改委的”“我是协会的,能加个微信吗”“这机器人能进(蔬果)大棚,对吧”……
在前不久结束的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全球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大会(以下简称“高促会”)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分区展台“变身”洽谈桌,不少高校的科研团队摊点纷纷展出了科技感拉满的新技术、新产品,来自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等单位的“买家”们不时抛出合作“橄榄枝”。
在本届中关村论坛年会期间,不论是平行论坛、技术交易会还是配套活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成为中外参会者提及的“高频词”之一。不仅有多所高校校长分享了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案例与模式,也有专家直面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谷”挑战。
科研人员往往将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过程称为跨越“死亡谷”,越过“死亡谷”,就意味着科技成果能够以商品的身份上架销售。
如何成功跨越“死亡谷”?这道大题急需新的解法。
高校科技成果“转”起来
在高促会“全球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主题展”展位上,一只白色的北极熊模具前站满了人,“摊主”却不见了。
“张凯老师昨天来了,今天又飞到厦门去了。”北京凝基新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卢迪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随着业务不断拓展,该公司董事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张凯的“行程单”越来越满。
卢迪介绍,该公司核心技术是不融化、不滴水的凝胶冰雪新材料,可以应用在文创产品、户外冰场、冷链物流等多个领域,由张凯教授团队研发。
2023年,北京理工大学开始全面推广“先赋权后行权”转化模式。学校先不入股,授权教师团队依托职务科技成果创办企业,待公司通过市场检验、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学校再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获得股权或现金收益。这一模式极大简化了流程,提高了转化效率。
张凯是这一新机制的获益者之一。手里有技术、学校给支持,公司仅成立一个多月就拿到千万元级别的融资。2024年,公司生产的文创产品“凉宝”相继在北京动物园、王府井大街等地“上架”,受到了市民游客的欢迎。
卢迪透露,目前,公司所有生产线已经能满足每年上百万个小“凉宝”的生产,但今年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做大”。他说,公司今年将在冷链物流、冰雪体验场景、绿色建筑、储能等领域拓展业务,例如为企业研发节能“冰被”、在不下雪的城市里打造“冰天雪地”活动场地等。
距离凝基新材展位不远处,北京工业大学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马雪梅亲自上阵,向参会者介绍团队研发的新型氢面膜、氢饮料等产品。“去年是成功研发,今年产品已经成功量产了。”马雪梅介绍,团队在创伤救治领域原创性地发现氢气引发全新的愈合方式,并基于此成果成功研发新型氢敷料系列产品。
记者了解到,主题展区向国内外高校征集了70余件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涉及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等领域,此外,全球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校地企协同模式、国家大学科技园机制和优质科技成果也面向参会者展出。
“大家心中的共识是,创新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和社会价值。”清华大学副校长曾嵘在高促会上表示,高校目前依然是中国创新非常重要的策源地。
日本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唐捷注意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还面临很大的挑战。她举例,根据《2024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我国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到53.3%,而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高校专利转化率为3.9%。
“中国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和转化的科技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还具有较大发展空间。”唐捷说。
科技成果转化为何遭遇“死亡谷”
今年年初,《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正式公布,其中明确提出“提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能”。
“科技成果转化被摆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那么,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它面临的挑战是什么?”论坛年会期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关村智友研究院院长王田苗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50人论坛上发问。
王田苗与中关村智友研究院的研究员们对比分析了美国、以色列、欧洲以及中国创新领域的科研论文、独角兽企业等信息,认为“小天才”创业和大厂高管创业,这两种方式最容易让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提高,例如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宇树科技CEO王兴兴等。他认为,这两类创业者都具有满腔热情和使命感;都具有商业思维,以市场需求为牵引;都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那么,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遭遇“死亡谷”或过早“夭折”的原因是什么?“市场需求不明确,现金流断裂,创业团队或合伙人的分裂。”王田苗说。
他提醒,在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格局中,要充分理解两个核心要点:一是国家战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迫切需求,二是必须回归市场牵引的商业本质。“只有实现转化生态、创新人才、产教融合协同等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找到有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方法。”
西北工业大学资产公司董事长、国家大学科技园主任符新伟提到,对高校院所来说,职务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存在分离的实际情况,这也是造成现在成果转化“乱象丛生”的原因之一。
他解释,成果完成人对成果的使用、处置,都具有相对话语权,但成果的所有权属于高校院所,要按照国有资产进行管理,这一对矛盾关系造成了成果转化的痛点,成果完成人更愿意选择转让、许可等相对简单且风险较低的转化方式,导致有组织的转化无法有效开展。
符新伟建议,亟需按照成果转化的规律,制定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具体操作路径。同时,坚持做有组织的转化,在转化方式的选择上要因地制宜、坚持最适合原则,不宜一刀切。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常务副会长雷朝滋在千校万企协同创新大会上也提到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的问题。
“企业要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这句话在雷朝滋看来,第一个阶段要让企业成为投入的主体,“不投入就不会关注,就没有内生动力”。第二个阶段,企业要成为科技成果运用的主体。第三个阶段,企业才有可能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跨越“死亡谷”,着眼校企“深度融合”
破解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谷”难题,国内外多所高校校长探索出了新的模式、机制,也有多位专家给出了破题之路。
上海理工大学校长朱新远分享了该校探索的作价入股先行先试机制。2016年,上海理工大学科技成果“作价入股”试点项目正式落地后,成功注册上海上理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并给予太赫兹技术团队72%的股权激励。“现在看起来没什么,但在当年这些举措都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做成了全国首单科技成果转化递延纳税优惠项目。”朱新远说。
“当前不管是在传统工业还是人工智能方面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韩国汉城大学校长李昌远列举了这所位于韩国首尔老城区的高校面临的科技创新挑战,提出了一种以产业振兴、面向未来的技术储备、城市创新纽带的“三维战略”,结合学校在AI、XR、机器人以及数字创意技术方面的积淀,与中国、东盟、欧洲等地建立全球创新网络,让高校在区域发展中主动担当。
“推动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其实就是为了把它(科技成果)用上去。”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张立群介绍,西安交通大学建设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汇聚政、产、学、研、用、金6种资源,推进企业主导的产教深度融合。
张立群还说,学校创立了“双院长—双管理—双签字”校企合作模式,如果企业一方的院长不同意某个项目或是不同意购买某个仪器设备,那么高校就不会强制花经费,以此来推动校企深度融合。
“过去老说企业是出题者,其实一定要(和高校)共同出题。”张立群说,企业和高校共同“出题”、共同“答题”的目的在于,把准方向,培育研发人员,等三五年成果做出来后,企业、高校师生共同受益、共同成长,“这才叫深度融合”。
雷朝滋认为,加强企业主导的校企合作,是破解当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难、产业化低的最有效途径。
雷朝滋还提到,为了让产学研合作真正深度融合,让高校老师对企业的项目有兴趣、有信心,高等学校的科技创新管理也要与时俱进,也要改变,一视同仁地对待校企合作项目。
唐捷曾参加过两个日本的科研项目,她认为,设立服务机构,产学研服务机构以及技术转让机构,能够促进高校与企业间的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形成独具特色的高科技产业园的合作模式。她提到,如今北京工业大学已经有了山河湾谷创新区,从短期目标、中期目标到长期目标推动校地产协同,推进产学研融合发展。
“我们的设想正在变成现实。”曾嵘向参会者展示了正在拔地而起的清华南口国重基地图片。他介绍,该基地集中承接清华大学以全国重点实验室为主的有组织科研力量,基地内还将建设幼儿园、小学、学生公寓等配套设施,预留产业转化中试平台。曾嵘希望,多个学科的科研人员在基地内实现学科交叉融合,校地企交叉融合,为国家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作出贡献。
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副司长舒华在千校万企协同创新大会上提到,要深化科技成果管理改革,加强校内科研、人事、财务、审计、纪检等部门间的统筹协调,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探索,健全尽职免责机制,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